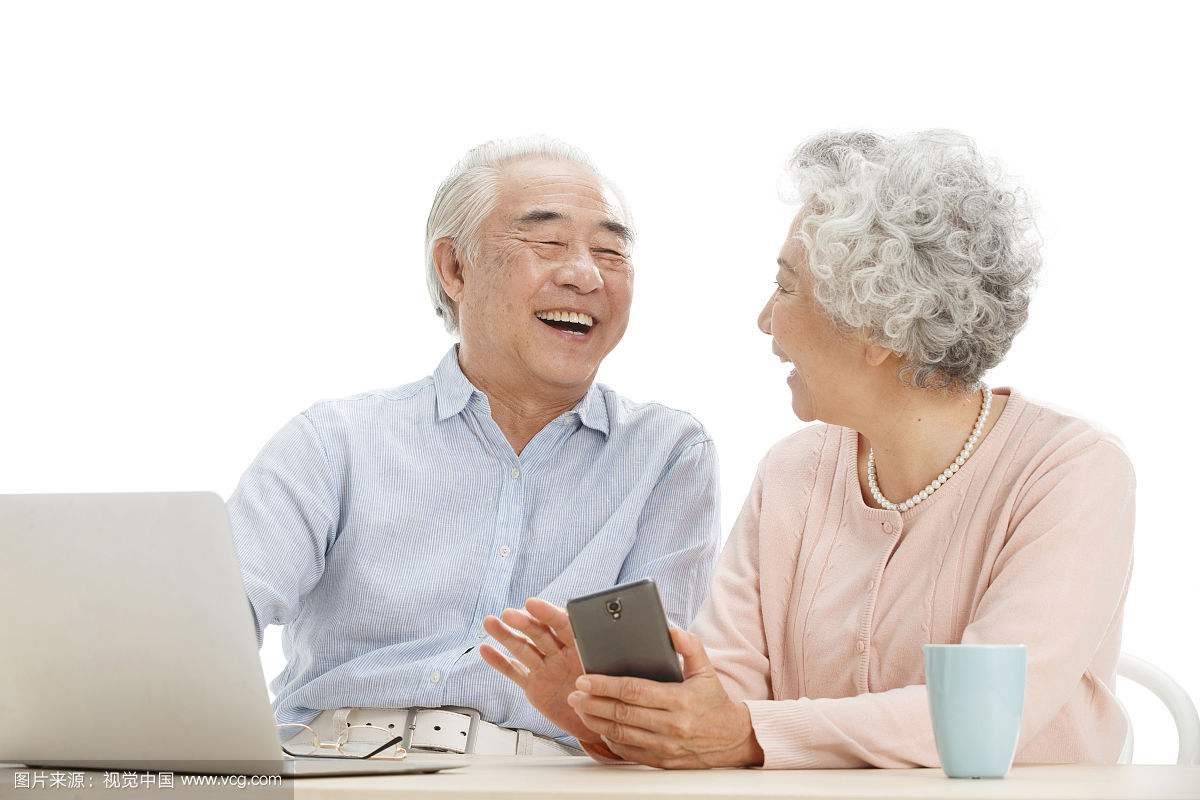-
限購·圈層·高考:先把河過了,再聊拆橋的事可好?
2017-05-03 15:17 識局
限購:
既然青春無處安放,那就請還鄉
4月20號清晨,在某市打拼的外地小伙伴們一覺醒來,發現終于不用再抱怨房價漲得太快了——前一天晚上,該市出臺了“史上最嚴限購令”,把外地人購買首套房的首付比例提高到60%。
“按現在的房價,到年底,我能攢夠三成首付。”一位小伙伴在電話里對我說,“所以最近特害怕漲價,覺都睡不踏實。謝天謝地,這下終于解脫了。”
他是用戲謔的口吻說這話的,但我不知道該怎么接——是恭喜他大徹大悟,還是埋怨他在落戶條件寬松的時候沒遷戶口?當然,說什么都晚了,他的命運已被改變。
其實他一直很努力: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努力加班、周末努力應酬;其實他也算挺有錢:30多歲的人,年收入20多萬,在那座城市屬于中高收入群體。然而這一切并不足以讓他逆轉命運的洪流,到達渴望中的彼岸。于是他漸漸明白,他永遠無法左右政策,而只能被政策左右,那也是命運的一部分;當然,接受命運是唯一的出路,只是不停變化的命運讓未來的圖景變得模糊,無所適從的茫然終于侵蝕了來日方長的期許,他已經很久做不到夢。
“夢”之所以被稱為“夢”,當然是說它未必實現;但它至少是個慰藉。在苦悶交織的時候,是它提醒做夢者:你有權以自己的才智和辛勞改變自己的命運,只要你足夠出色、足夠努力,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立足。可是如果它換一種說法:即使你跟這里的土著一樣聰明和勤奮,也永遠成不了他們,還是回到你自己“應該在”的位置上去吧。那它就不是夢了。
起點可以是不公平的,但夢總該是公平的。
我下意識地望向窗外,已經在風雨中褪去顏色的樓盤廣告讓我忽然想起了那句著名的廣告語——“不要讓這座城市留下你的青春,卻留不下你”。現在倒好,有些城市連你的青春也不打算留下,你可以走了。
不過這倒給了我安慰小伙伴的靈感:“幸虧你還年輕,就算不能落戶,還能換個地方,總比那些拼了半輩子還‘漂著’的人強。你肯定不是最慘的,你買不起那里的房子,別人也買不起,大家都一樣。”
小伙伴哼了一聲。“是普通人都一樣。”他糾正道,“有家底的人無所謂,就是全款他也買得起,還有那些有門路、有資源的人,人家根本用不著為限購發愁。真受限制的也就我這種人,當然還有普通的炒房客。其實我也討厭那些炒房客,可是你想,什么人炒房啊?大多是些有錢但沒門路的。他們不炒房,難道炒股嗎?還是天天看著錢存銀行里貶值?”
我再次噎住。“何況就算普通人,也不一樣。”小伙伴則繼續說,“你這種早已上岸的,還有機會往上走,我這種新來的,連你的機會都沒有了。”
這次我真的無話可答。我明白他的意思:我比他早參加工作三年,早買房三年,由于有房在手,所以成功“晉身中產”;他家境不比我差,水平不比我低,付出不比我少,但“中產”這道坎,他竟邁不過去。
再往上那道坎,我也邁不過去了;而他,還沒資格去想。
▼ 圈層: 這不是最好的時代,也不是最壞的時代 不知不覺,又扯到了“圈層固化”的話題。 這個話題最近被扯得太多,我真沒啥可扯的了。只是有件事可能要澄清一下:“圈層”這個東西真的是最近才出現的嗎?它可以“像以前一樣”完全消除嗎? 這要從它的源頭說起。 看《權力的游戲》,我們覺得史塔克家族好高尚,而小指頭好卑鄙;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我們覺得白淺好高尚,而素錦好卑鄙;看《人民的名義》,我們覺得侯亮平好高尚,而祁同偉好卑鄙。然而,前者固然是真·高尚,但他們高尚的原因之一是,他們用不著卑鄙。 人類總覺得容易得到的東西沒什么了不起。那些生而富貴的人,通常不太渴求富貴;而那些做出成績有人看見、捅了簍子有人兜底的人,也不太需要權謀心術。于是,高尚的他們,不容易理解其他人為何不能像他們一樣高尚:有事明著來不好嗎,干嗎玩陰的? ——大哥,您有人罩著,當然可以跟我明著來;我沒人罩著,要是跟您明著來,我來得過您嗎?當然,您要是說,我來不過您是正常的,這一點從我生下來那刻起已經注定了,那我無話可說。 底層人可以“憑真本事往上爬”嗎?在理論上當然可以,但前提是,你得有個好心態。比如碰上梁璐,愿意再等十年再提拔,或者一輩子不提拔;比如碰上限購,愿意再等十年再買房,或者一輩子不買房。 這真是一件特別難講的事。梁璐和限購的持續時間都不是你能決定的,有些人等著等著,就等來了機會,也有些人等著等著,就等來了圈層固化。不過,就算等來的是后一種情況,也沒啥可抱怨的,因為這是一種必然。 每個人都有一種本能,那就是用盡各種手段鞏固自己的地位,而不是別人的地位;每個父母都有一種天性,那就是想方設法把資源傳遞給自己的子女,而不是別人的子女。 事實上,圈層固化才是人類社會一直以來的常態,“將相無種”反倒是動蕩時代給人造成的幻覺。何況將相真的無種嗎?歷史上的大一統王朝,只有西漢和明這兩個朝代的開國皇帝是真正的草莽出身,其他人則莫不跟當時的上層社會有著血緣或裙帶聯系。就連成吉思汗和努爾哈赤這兩個來自“邊鄙之地”的君主,也是世家酋長的子弟,他們的眼界和號召力,是經過了數代錘煉的。你還真當他們是放牛的王二小? 當然,過去的大多數人并沒意識到圈層固化的存在。這一方面是因為,人們被封閉在本鄉本土的小圈子里,放眼望去,最牛的人不過是本村的士紳,感覺不到巨大差距;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科技和制度都很落后的情況下,普通人拼命勞動,也就剛剛能吃飽飯,完全沒有精力去思考“吃飯”之外的問題。太過稀少的上升機會壓抑了上升的欲望,讓很多人既不抱怨“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也不渴望“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一切跟他們彷佛沒什么關系。 直到有一天,人類科技進步了,機會變多了,放牛娃也能升官發財了,小仙也能飛升上神了,大家才發現,哦,原來圈層還挺固化的喲,平民子弟想跟世家子弟平起平坐還挺難的喲。 廢話。不難能叫“雞變鳳凰”嗎,這可是基因突變的大事啊。 所以我必須提醒大家:不要以為現在的圈層固化很嚴重,真正嚴重的固化,是絕大多數人壓根意識不到“固化”這回事的存在。而當我們一邊吃瓜一邊抱怨圈層固化的時候,往往是圈層還不太固化、上升通道剛開始收窄的時刻。 我們該感謝這個信息時代——它或許讓我們感到痛苦,卻幫助我們擺脫了無知。人們不是經常抱怨“從前咋沒這種破事”嗎?其實“這種破事”可能是從前真的沒有,也可能是從前一直就有,只是沒人報道,所以我們不知道它有。要知道,“個體印象”總會受到媒體影響,比如很多人覺得現在碰瓷現象很多,但真正親身遇到過碰瓷的人有幾個?大家之所以有這種感覺,多半是因為獲取信息的渠道比之前廣了,知道的事也比過去多了。 圈層固化的道理也是一樣:它早就在那里了,只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看見它在那里,就越來越看不順眼。 而已。 ▼ 高考: 它不是最好的選擇,但可能是最不壞的 人類對付自己看不順眼的東西,大致有三種辦法:第一,讓這個東西消失;第二,閉上眼不看;第三,說服自己,這東西其實挺順眼。 我不知道大家會采用哪種辦法,反正在我看來第一種不可行,第二種不長期可行,第三種可行但不舒服。于是,對付圈層固化的可行方案,就只能是承認它的存在,但在不同圈層之間保留一條公平的上升通道,給大家留點希望。 你知道嗎,其中有個通道叫高考。 我猜很多人會對這話嗤之以鼻:別扯犢子了,這都啥年代了,還說高考呢?你看不見清華畢業生買不起清華旁邊的學區房啊。 對此我想說,這話沒錯,但你有更好的辦法嗎?如果你能找到比高考更管用的合法途徑,讓沒背景、沒門路、沒家產的孩子買得起清華旁邊的學區房,我立馬把高考罵得一文不值,我早就想這么干了。 高考肯定是不完美的。過去人們抱怨它是獨木橋,嫌它太擠;現在高校擴招,它成了鋼結構斜拉橋,人們又說它豆腐渣工程,罵它坑爹。我能理解大家的怨氣,然而怨氣的根源在于,很多人過了橋還是無路可走。 可這不是橋的問題。三十年前普遍發生、二十年前經常發生、十年前還偶有發生的“寒門貴子”現象,讓我們習慣了“十載寒窗,一朝騰達”的套路,以為這是天經地義。我們忘了,橋那邊的路也不寬、車位也不多,以前過橋的人少,路和車位還夠用,現在過橋的人多了,而早已過橋的人又占據了好車位,后來的人當然要被堵在路上,甚至堵在橋頭。 但問題是,除非你能證明“上橋”本身就不對,不上橋反而路更好走,否則你還是得上橋。這是個很現實的道理:過了橋,可能有路也可能沒有,不過橋,幾乎肯定沒有。 注意:上述道理僅對家境一般的普通人有效。如果你有韓寒的天賦,或者你有投胎的天賦,就當我什么都沒說。 我真的不想絮絮叨叨勸大家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那太俗了,可現實就是這么俗。何況,如果你以為我寫這些,只是為了勸大家珍惜高考沖刺階段的時光,那你就太俗了。我的目的是勸大家珍惜應試教育階段的時光。 是的,你沒有看錯,我也沒有寫錯。 你可能以為,應試教育的全部意義就體現在高考那兩天,但實際上,它的意義體現在你人生中的每一天。因為它培養你的韌勁。 學習從來不是什么“快樂的事”,學語文數學固然不是,學彈琴繪畫也不是,甚至學打籃球跳街舞都不是。難道達·芬奇是因為畫雞蛋讓他快樂,才去畫那成千上萬個雞蛋的嗎?難道科比是因為做深蹲讓他很爽,才堅持每天早起做力量訓練的嗎?他們又不是神經病,誰喜歡干那些既枯燥又累人的事? 人類的天性傾向于“放松”——去KTV里吼幾嗓子,多么舒服;上扎啤攤喝幾杯啤酒,多么痛快;拿起手機玩幾局游戲,多么輕松!可是你會發現,唱完歌,過不了一天還想唱;喝完酒,過不了兩小時還想喝;放下手機,過不了五分鐘還想拿起來。 越是強烈的快樂,它的“半衰期”往往越短,所以你越追求這種快樂,就越會上癮。你必須不斷地重復這件事,讓它不停地刺激你的神經,直到它讓你變得浮躁、淺薄、茫然,再也無法專注于真正重要的事。 于是,你的人生停滯了。你只能重復現在的生活,再不能向前邁出一步。 所以我們看到,專業人士會找時間放松,但不會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圖痛快”。比如球星很可能也會去KTV里唱歌,但在訓練場上,他不會只憑自己高興隨便耍幾下。他要做枯燥但必不可少的訓練。 學生也是一樣。你必須在應試教育階段學會做那些不快樂但有益的事,并讓它們成為習慣。如果在這個時期不能鍛煉出勤奮嚴謹的品格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即使過了高考的橋,即使橋前面還有路,你也不知道該怎么走。 那么剩下的問題就是:只有應試教育能培養學生的韌性嗎?難道素質教育不行? 這個問題很復雜。 ▼ 結語: 是應試教育有罪,還是我們的理解有問題? 大家通常以為,“應試教育”等于“死記硬背”,它訓練出的學生“高分低能”,完全沒有獨立思考和生存的能力;大家通常還以為,要從源頭上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釜底抽薪”、改革高考,讓它更加靈活和多元。這話當然沒錯,但它對應試教育的理解可能并不完整。 應試教育的精髓恰恰在于,它要“應試”,也就是只要考試還存在,它就會跟著存在;而考試的精髓恰恰在于,它必須是標準化和程式化的,這雖然死板,但很公平。 我們能找到比考試更好的選拔人才的方法嗎?前面說了,目前還沒找到。那我們可不可以打破考試的死板,卻保留公平呢?這個好像還靠點譜,比如我們可以考察學生的審美素養,嗯,讓每個學生畫一幅畫怎么樣…… 這算是“考察綜合素質”吧?然而當你發現,你上司的兒子用一幅比畢加索還抽象的畫得到全場最高分的時候,你恐怕不會贊成這種“考察”。相反,你會懷疑這個得分究竟反映了學生的真實水平,還是受到了場外因素的影響,可你又不能質疑,因為“美”是沒有統一標準的。 這就是為什么除了作文,高考的其他部分都有統一的標準答案;這就是為什么就連作文,也要設置統一的參考答案和“八股范式”。要是沒有統一的標準,考試成績何以服眾? 但這樣一來,應試教育就不可避免產生一種副作用:既然教育的目的是應試,那只要把考試應付過去就完了;既然有標準答案,那只要把標準答案記住就好了。至于學生是通過自己的思考得出答案,還是被老師逼著硬生生記住答案,無所謂。 也就是說,“死記硬背”并不是“應試教育”本身,它只是一種被“應試教育”催生出來的捷徑。這種捷徑確實有害。 習慣于等別人告訴自己答案、而不是自己獨立思考的人,容易被“大流”迷惑,只要“大家都這么想”,他也就跟著這么想。他既不知道,有時候“多數”只是一種通過渲染和灌水營造出的表象,也不會認為,就算大多數人真的這么想,“這么想”也未必就是對的。他只會理直氣壯地冷笑:難道大多數人還能都錯了? 但這是應試教育的問題,還是應試教育內容的問題? 另一個被經常拿來罵應試教育的現象是,如果只是“記住”標準答案,而不是去“理解”它,會形成一種過分關注“正確”和“錯誤”的思維模式,這樣的人往往不能接受黑與白之間的灰色,不能理解對與錯之間的現實。在他們的腦海里,世界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但這是應試教育的問題,還是應試教育方式的問題? 應試教育是應該改進,但“改進”跟“取消”是兩碼事。我也不反對素質教育、快樂教育,但所謂“快樂”,應該是通過啟發學生的獨立思考,讓他們在學習中發現快樂,而不是讓他們以“快樂”的名義放縱自己,忘記前面路上還有個高考在等著他們。 畢竟正如我反復說的那樣,他們要先過了高考這座橋,才能談該不該拆掉它的問題。
免責聲明:本網站所有信息,并不代表本站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請自擔。
上一篇:美聯儲縮表的影響
- “一哥”王亞偉產品遭遇秒殺 “踩點”這9家上市公司
- 女子路虎停馬路邊 一夜之間成“光桿司令”!
- 2017年12月4日1歐元兌換多少人民幣
- 馬云:人類要自信可控制機器 未來貿易屬于中小企業
- 世界互聯網大會:除了人工智能,這些議題與你息息相關
- 迅雷內訌最新消息:究竟是中場休息 還是告一段落?
- 2017年12月4日一元人民幣是多少韓元_韓元換人民幣查詢
- 2017徽商銀行理財產品有哪些?徽商在售理財一覽
-
1/ 無照駕駛56年!老司機為躲避交警查 竟想到這些招 絕對實用! 52124
-
2/ 2017民生銀行理財產品有哪些?民生在售理財產品一覽 51033
-
3/ 重大突破:石墨烯電池12分鐘充滿,這兩只股票要起飛! 48023
-
4/ 重磅!騰訊市值超Facebook躋身全球排名第五名 46019
-
5/ 愈挫愈勇!“當代愚公”二次創業,重整匯源河山! 45214
-
6/ 軍報再評紅黃藍事件內幕:事件背后大股東資本野心被曝光! 44281
-
7/ 股市娛震:《我的前半生2》女主竟然換成她!網友直呼“沒看頭” 44133
-
8/ 12月4日周二財經早參:新聞聯播也說話,今年高送轉基本廢了! 44112
-
9/ 12月1日周一財經早參:道指破兩萬四帶給我們的啟發! 43294